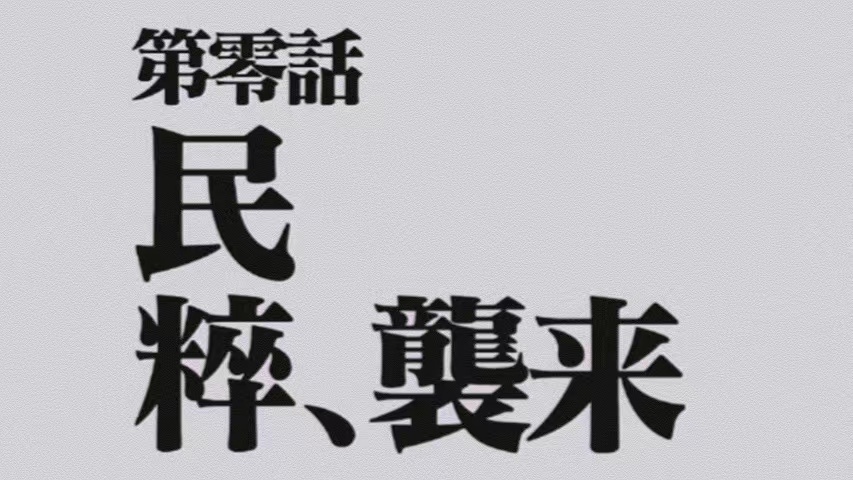
|刘擎
“……(民粹主义者)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的特点,他们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与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民众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彻底改变腐败和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
近十年来,民粹主义(populism)在西方公投、改革等事件中频频出现,并在媒体报道中与愤怒、贫民、反精英、反建制等词相关联,在众多官方媒体口中,民粹主义已然变成能够终结西方民主进程繁荣的洪水猛兽,更有甚者,在最近已有部分学者预言,身份政治主导的民粹活动以将美国推向风口浪尖,甚至最终将可能导致美国新内战的发生。事实是,事到如今,学界一直没有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定义(虽然对民粹主义早在19世纪60年代对农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并且这一术语在上世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已经产生),也难以辨明其本质特征。扬-维纳尔.米勒(Jan-Werner Müller)对过去学界的研究方式进行了批判分析,并跳出历史偏见、自我评判的误区,鲜明指出民粹主义的七个核心要素:
- 民粹是必然的、消极的;
- 批判精英、反多元主义是民粹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 民粹对人民利益代表具有垄断倾向;
- 民粹可能需要通过借公投上位,但最终会抛弃民主制度;
- 民粹执政并非一定失败;
- 对民粹的态度应是批评而接触,思考问题而忽略逻辑;
- 现在民主政体确实未必靠近底层人民,但民粹一定不是一方良药。
什么是民粹主义
在传统视角来看,民粹主义似乎具有许多非独有的特征,例如反建制、仇视精英、仇视富人、排外、愤怒……米勒指出,过去对民粹的研究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方面是带有历史偏见与地域差异,例如民粹主义常常被与农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贴合,这与民粹发端于农民与地主争斗的历史背景分不开,另外民粹在欧洲与美国也带有不同的政治色彩,在欧洲,民粹偏向于反对多元主义的、煽动民众的、不负责任的,但在美国,民粹反而是贴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的、草根的;其次,对民粹的认知是片面的,例如过去常常认为美国左派民粹(特朗普为代表)的主要支持者是穷人,但根据机构的实际调查发现,民粹的主要支持者主要是白人,穷人支持率最高的反而是希拉里(由此可以印证后面民粹对人民定义垄断的特点);再者,由于民粹的政治主张倾向于道德化(见后),媒体在引用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怨恨”“愤怒”等词语,这一做法实际将讨论引入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将民粹信众引入弱小、底下的地位,这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合(例如在美国仍然占据多数的白人,已然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少数者”)。
那么,民粹究竟是什么?米勒认为,民粹最重要的“界定性特征”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即民粹主义者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认为
在代议制的政体中,唯一能被检验的是选举结果,而所有其他东西都是“超政治的幻觉”,全体人民从来不可能被认识或代表。
汉斯.凯尔森
虽然民粹是出身于代议制政体,但这种鲜明特征无疑是向威权政治或是人民主权政治的靠拢,也就不可避免地背离了二战后西方社会最看重的分权制与多元主义,民粹要想维持其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原则,就必须放弃社会的多元性,抛弃、压制部分民众的意志与利益。然而,这种代表性是片面的、狭隘的,民粹代表的是狭义的人民,它认为是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群体,是同质的、永远正直的,由此存在单一的、公共的利益,引导民众清晰认识、努力争取。
从这一核心特征下,民粹又衍生出若干重要的特征:
- 民粹一定是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崛起的唯一道路是对人民概念的垄断,而西方愈发成熟的技术官僚体制(背后代表着精英阶层利益)无疑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并且这种对立方法、斗争形式也推动民粹将政治诉求道德化,甚至可能上升到对敌对党派领袖的人身攻击。然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民粹反而能够免受这种道德攻击的伤害,因为民粹引入了新的政治道德判断标准:评判政党的标准应该是工作与否(反对技术官僚),例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曝出贪污事件之后毫发未伤,因为民粹对人民代表的高度垄断使得选民有种政治错觉:民粹主义者贪污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民粹代表的人民是狭隘的人民(如前所说)。在西方,自希腊文明以来,人民有三重含义:整体的人民(政治有机体),平民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整体的民族(文化角度),从人民含义上来说,民粹并不是为平民百姓而奋斗,而是将整体的人民分裂成贵族与平民(甚至是更狭义、更小范围的平民),并加以挑拨对立。
- 民粹不反对代议制、不反对公投、也不会在执政后快速灭亡。民粹仇视精英是因为他们寻求对人民概念的垄断,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新的精英阶层执掌政权,并通过契约的方式被人民授权成为传话筒(贝佩.格里洛(五星运动):“你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我来扮演扩音器的角色。”),让人民有种民粹的决策有种“人民指使的”的政治错觉;同样,民粹需要全民公投的形式来证明他们是“多数人民”的代表,但他们不希望选民们长期参与政治,他们期望的是监护人式的家长政治。同时,事实证明民粹执政后并不会立刻自取灭亡,他们执政期间仍可以把失败推给暗中作祟的精英阶层。
- 民粹的最终道路是走向威权政治、人民民主专政,是走向反多元主义与舆论控制。民粹想要维持其对人民的绝对合法的垄断代表,就必须挑战权力愈加分散的西方政体,但二战之后西欧就对人民主权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也正因此民粹主义者无法承担直接施行威权政治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代价,而是不断向代议制的底线挑战。同时,为了控制其统治力,他们对舆情加以控制,批评、惩处反对意见的媒体,并将它们定义为境外反动势力。
- 由于上述特点,民粹创造了三种鲜明的治理方式:对本国政治与舆情的殖民与垄断(比如占领无党派人员行政岗位、惩处新闻记者)、施行恩庇政治(用物质、非物质的恩惠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这实质是财团控制模式的异化,过去选举是财团投讲演、民主政党等方式控制选举,现在是跳过中间商,民粹主义者通过寻求资金帮助或许诺未来的方式直接争取选民。)、歧视性法制主义(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受完全的法律保障,只保护属于人民的人。这比之人民民主专政更加不“自由”,人民民主专政只限于公民身份、拥护党政领导,而民粹上升到了肤色、血统、民族、财富等,应当是新纳粹主义)
弑母的俄瑞斯忒斯
应当指出,民粹是依靠代议制产生的,但它只是在盛行的代议制民主下对威权政治和人民主权的妥协,它的最终出路是消灭多元主义、激化民族矛盾、走向高度集权,如米勒所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应被理解为民粹主义活动,只是展现出某些其他特征,如暴力美化、种族主义、激进的“领袖原则”等。
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依然成熟的资本世界,政治的关注中心不可避免转向了公共事务利于,由此身份政治等的流行成为民粹滋生的土壤,由此民粹的产生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民粹是代议制民主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
但民粹是不科学、注定会失败的。以马哲的矛盾论来说,民粹诉诸人民的划分是单一纬度的,这意味着其政党代表的是意志是静态的矛盾对立面,一旦矛盾转移、变化,其垄断地位将不可避免地消弭,从而人民将不再成为人民,而变为少数群体,直至新的人民选出新的民粹代表。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当权、又被抛弃的人民将与社会、政府产生心理隔阂,最终导向内战或是无政府主义。李筠在《西方史纲》中有句话说的很好:
“西方是中国理解自己最重要的他者……他者有更厉害的逻辑:它不只是让我们在比较中认识自己,还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它的样子塑造自己,哪怕你讨厌它、甚至憎恨它。”
李筠 《西方史纲》
西方亦然。无论西方是否愿意承认,信息时代以来西式民主已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哪怕自冷战乃至二战以来,欧美各国极力抵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毫无保留地鼓吹分权制民主制度,最终这种自由至上的民主也无可避免地发现自身的矛盾,西方社会不可避免地走进非民主的陷阱,民众需要利用民主程序强制变革,从公司财阀、精英阶层手中重新把控自由的权力,但这种行为恰恰是正义却“反自由”的。这也就是卡茨.穆德(Cas Mudde)所说的:
(民粹主义是)以反自由的民主方式,对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回应。
卡茨.穆德
然而这种向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靠拢却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就如中国曾经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一样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无论如何改革、如何粉饰、如何收买选民,资产阶级当权者所维护的只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是大部分人的单一的利益,在追求多元化的道路上,代议制只能被不断出现的社群、亚文化群体、新型身份群体的诉求拖累尚,如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认为:
”’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最终会否定冲突与异议的合法性,而这时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
尚塔尔.墨菲
而在反多元化的道路上,民粹又无法克服短视的眼光,只能争取静态人民的利益,一旦矛盾发生转移,这种高压统治就将土崩瓦解。民粹就如同弑母的俄瑞斯忒斯一般,它从代议制民主中诞生,却又以“消灭”代议制民主为目的,无论其是否能够成功,最终都只是失败的悲剧。
而米勒认为,西方民主应对民粹的方法,应当是发挥代议制民主优势,积极与民粹对抗,从而实现进化,就好比过去西方对人民这一概念定义的边际问题探讨一般,“努力过,失败过,没关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每一次失败都比上一次失败得更高明。”他认为,自由民主应当排斥民粹而非忽略民粹,应当严肃对待他们的政治诉求,但大可不必了解他们的分析方式。这应当是冷战后西方世界最严峻的挑战。
民粹可能存在于中国吗
观照民粹主义,是否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说,民粹是诞生、寄生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政体下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本身是自由民主的畸形变体,因此在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并且已经是人民主权当政的中国,民粹自然完全谈不上存在。并且,民粹主义应当是中国重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机遇,它恰恰说明即便资本主义给他们的“自由信徒”许诺建设一个美好的伊甸园,最终也无可避免将面临上帝的怒火——身份政治、种族主义、边缘群体的狂袭,米勒建成了一艘方舟,很多其他理论家也是如此,但这些方舟是否是泥菩萨,当下仍未可知。
但是,我们中国本身也应该从中看到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虽然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很好的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多数利益,但其中仍有许多被我们忽视的群体,例如三和大神、留守儿童,即便是我党最关心的农民工的利益,在某些地域黑恶势力泛滥的地方仍不时受到侵害;再比如近年来对媒体的加强监管保证了思想文化建设,保护了免受境外势力的破坏,但同时是否无意识地阻碍了一些公民检举、发声的渠道?又该如何疏通、保护这些渠道?再者,米勒也指出,西方社会所谓的街头抗议、网上请愿虽然有着真实的民主含义,但缺少有效的民主形式,实际无法对抗代议体制。那么放眼国内,又该如何更好地加强法治进程、保护人民的利益?举个例子,网络已经部分取代了传统政党作为中间媒介的身份,“自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以来的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对影响力的节制(他们所称的中间机构)都消失在乌尔比纳蒂所说的“直接代表”下之下。同样,任何与我们已有的想法相抵触的东西,都在互联网这个回音室中被消音了。网络(以及特朗普这样的领袖)总会有答案。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答案总会是我们期待的。”我们又能否从网络下手,让出部分权限,连接基层与中央,实现对中间级官员的监督?
总结
无论深受“荼毒”的西方也好,事不关己的东方也好,民粹主义不可避免地再次催动着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借鉴,这是从最琐碎、最细节的公共事务领域向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再反思、自我改良,不仅逼迫着傲慢的代议制丢下尊严与成见,重新反思对多元主义狂热的追求,同时也警醒着中国,时刻自省,排除风险,跳出兴衰的历史循环。
端木莽子
2022/10/17 于二十大后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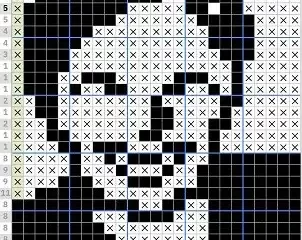


0 条评论